1993年,當約翰·卡馬克在id Software辦公室敲下最後一行代碼時,他或許並未意識到,自己剛剛埋下了一顆改變遊戲工業的核彈。
這個名爲“DOOM”的惡魔剋星,不僅炸開了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潘多拉魔盒,更將整個電子遊戲行業推向了技術革命與文化震盪的雙重漩渦。

FPS的空間革命
在《DOOM》問世前,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關卡設計,只能被禁錮在自同爲id Software開發的“僞3D”FPS遊戲——《德軍總部3D》的平板迷宮裏,玩家也只能在毫無起伏的平面地圖上直線移動。
但是身爲“DOOM之父”之一的約翰·卡馬克,卻硬生生在像素堆疊的牆壁上鑿出了高度差、斜坡和隱藏通道。
我在查閱資料的時候看到有當時的玩家說到:
第一次躍過血色岩漿,俯瞰腳下深淵時,那種垂直空間的解放感,就像人類第一次從熱氣球上俯瞰大地。
至此,《DOOM》打開了電子遊戲的第一場空間革命,FPS遊戲的關卡不再是單純的迷宮,而是成了“會呼吸的戰場”。

暴力美學的獨特浪漫
從最早的《DOOM》中就可以看到:
滴落岩漿的牆壁、扭曲的惡魔面孔、從血池中升起的石柱,這些用像素構建出超現實的地獄圖景,已經在暴力美學的催化下,成了衝擊玩家眼球的視覺炸藥。

而這其中的浪漫,則是暗含對人性本能對暴力美學的浪漫化解讀。
Doom,毀滅戰士,其無休止的殺戮既是對惡魔的復仇,也是對秩序崩壞的極端反抗。
這種設定將暴力詮釋爲一種打破規則、釋放原始力量的自由象徵,呼應了尼采“超人哲學”中“超越善惡”的浪漫理想。
類似的設定,在後續的《死亡空間》等遊戲中,均能隱隱約約看到。

網絡對戰的原始爆炸
在寬帶尚未普及的年代,《DOOM》的局域網對戰模式就像部落原始發現火種。
四名玩家擠在大學機房的終端前,操控惡魔互相廝殺,鍵盤敲擊聲與爆炸特效交織成原始的電子交響。
這種共享的暴力狂歡,比《反恐精英》的戰術對抗早了整整七年。

這種對戰模式催生了早期電競文化。
1994年,"DOOM Tournament"在達拉斯大學舉辦時,參賽者用電話線連接調制解調器,24小時不間斷的死亡競賽讓服務器幾近熔燬。
這種草莽競技精神,成爲日後《使命召喚》聯賽與《堡壘之夜》直播文化的遙遠前奏。

MOD文化的基因裂變
當《魔獸爭霸》的RPG地圖還在萌芽時,《DOOM》的WAD文件格式已經成爲玩家創作的潘多拉魔盒。
從再現《異形》場景的"Xenomorph WAD",到將馬里奧角色植入地獄的惡搞MOD,玩家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者,而是成爲了內容生產的原生細胞。
這種創作生態改變了遊戲工業的進化邏輯,甚至是因此而聯通了玩家與遊戲廠商。
甚至連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們今天在Steam“創意工坊”中看到的五花八門的創意,其種子竟然都來自《DOOM》。

而以上的這些深遠影響,僅僅是我從書籍和查閱的資料中所看到的,對於身處電子遊戲行業的從業者來說,想必會有更深切的體會。
多年來,《DOOM》收穫的讚譽和榮耀不計其數,它成功入選世界電子遊戲名人堂,足以證明它在全球玩家和遊戲從業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另外,如果你對《DOOM》這個經典IP想要了解更多,以及對id Software的崛起之路感興趣,我推薦你讀一讀《DOOM啓示錄》這本書。
它爲我們呈現了一個充滿激情與創新的遊戲世界,也讓我們看到了創業的艱辛與成功的喜悅,更有兩位創始人的“雙J傳奇”,包勵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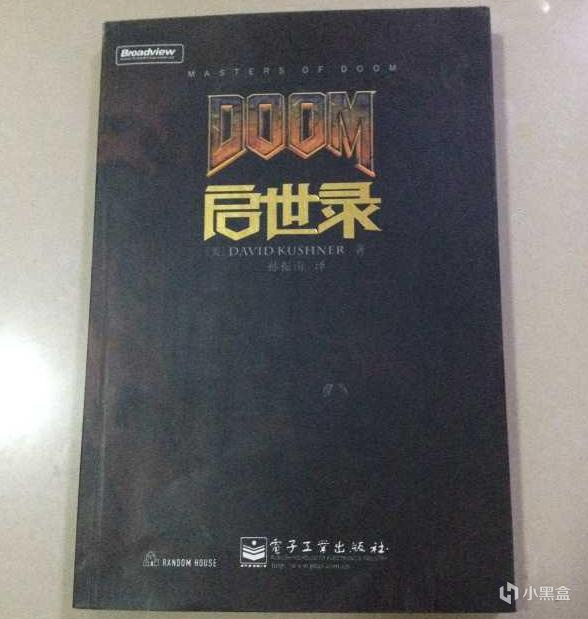
最後,我還是想引用文章的標題作爲結尾:
在世界電子遊戲的名人堂,《DOOM》就是當之無愧的GOAT,當BFG-9000的槍聲響徹在電腦時,我們所看到的——
是那顆1993年種下的惡魔種子,在每個遊戲世代都開出了新的血色之花,如同id Software創始人之一的約翰·卡馬克所言:
“通往地獄的唯一道路,是穿過屏幕。”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