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导演BK离开了从事十多年的电竞行业开始创业,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做了一个游戏纪录片公司,并采访拍摄了几百位顶尖的游戏从业者。
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全球华人中,唯一一个只做游戏纪录片的公司。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小众的事情?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他的钱从哪来?
——————————————————————
一、上海的大食堂
我在上海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不只是这座城市的繁华,还有大食堂。
如果我盯着一种食物点,饮食相对单调,导致我手上经常长倒刺,甚至开裂,嘴里头还容易长溃疡。
奇妙的是,一旦我改去食堂吃上两天,这些症状就会竟然缓解、消失。
我至今都觉得有点神奇,大概是因为食堂的菜肴丰富、营养均衡。

当然,除了饮食均衡,我现在还要关注血糖和胰岛素。
因为血糖不稳,我时常需要在采访或节目正式开始前补一针,生怕聊着聊着就会出现不适。
这样的生活节奏,既让我对身体有更深的自觉,也让我对“珍惜当下”有了新的理解。
二、“BK”的由来
“BK”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简短,却来源已久。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98年我玩CS的时候,需要一个英文名字。
我那会儿在自学吉他,而知道蓝调吉他大师B.B.King,就觉得得用个类似的名字,不仅致敬一下大神,也简洁好记。
后来创业要注册商标时,发现“B.B.King”这名字注册不了,就缩写成“BK”一直用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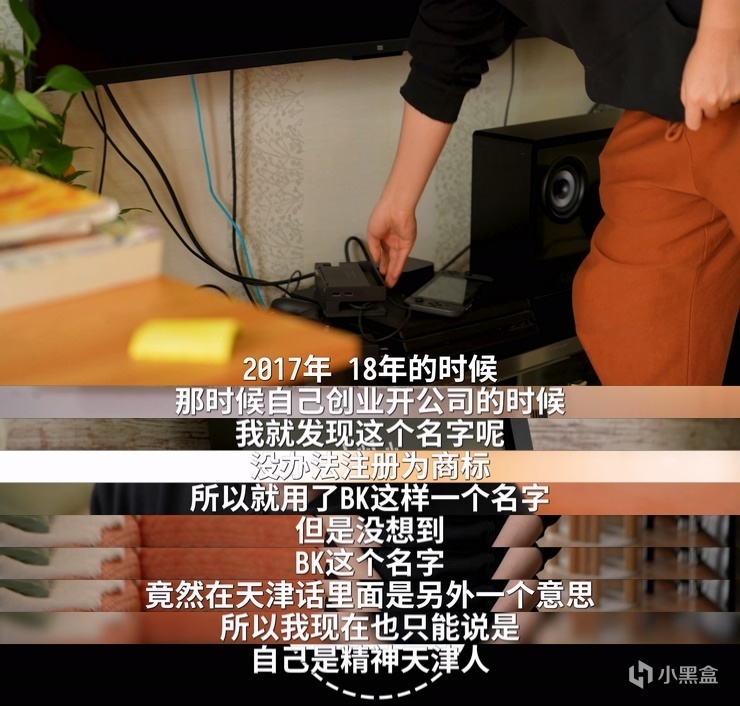
虽然我家里囤了各种游戏机和掌机,但一直没培养出用手柄操作的习惯。
小时候在偏远地区,其实见不到什么主机游戏,再加上我从小就对自己“其实没那么擅长玩游戏”有清晰认知。
我直到大学才在别人宿舍里第一次见到PS2,非常好奇:那黑盒子是啥?
于是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喜欢用电脑玩游戏。
三、电竞启蒙
在我那会儿,大家并没有“电子竞技”这个概念,只说“打比赛”。
记得高中时我们年级组了个“color”战队,每个人都取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们喜欢和别的年级甚至别的学校“约战”打CS,过瘾又带着些年轻的“中二”气息。
团队作战感十足,对我吸引力很大,我也很喜欢用狙击枪。

后来我考到西安,学的是计算机。
其实那并非我所热爱的专业,我更偏爱写作和采访。
不过因为堂哥选了文科,家里人就让我选理科,一来“家里孩子总得有个理科的嘛”,二来也觉得我的数学成绩凑合。
虽说如此,我进入西安后,意外地接触到极其浓厚的电竞文化。
当时国际赛事也陆续把西安纳入赛区范围,我在那一时期里做过赛事筹备、活动报道,逐渐在电竞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四、初入上海
2005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WE战队要在上海成立,需要一个能搞商务的人。
我就揣着我妈偷偷给我的2000块路费,坐上去上海的车,正式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电竞打拼生涯。
公司给出的薪水是4000多块,对一个年学费只有5000、只带2000块启动金的人而言,简直像做梦一样。
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我把现金取出来摊在床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数,乐呵得停不下来。

那段日子虽然物质上并不奢侈,但我有干劲、有激情。
2006年,我们用“草台班子”的方式租下了长宁国际体操中心,想做一场现场4000人的电竞赛事。
钱是东拼西凑来的,人手也就那么几位,但我们依旧成功地让观众坐满了场馆,用P2P技术把比赛转播给二十多万人,硬是扛下了暖气费、网费等各种开销。

五、转战电视台
到了07年,我发现一年只办一次比赛的模式学不到新东西,就转去了“游戏风云”电视台。

当时我想试试更专业的影片制作,也想提升自己。
可惜到了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赞助商倒闭,很多人失业。
游戏风云多个月发不出工资,我也被迫花光所有积蓄,还只能靠三把挂面和一瓶醋度日,撑了一个多月。
那会儿又挣扎又兴奋,因为我已能独立剪片、策划内容,内心里仍对游戏与节目充满希望。
并且,当时的整个大环境里面是没有的类似节目。
所以很快我的片子就到了频道的收视率第一,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正反馈。

等到10年,技嘉科技这家曾给我们赞助的公司,重新把散落各地的老同事召集起来,说经济危机过去了,把过去的游戏推广和活动运营接着干。
我们于是再次重振旗鼓,成立了新的电竞公司。
彼时优酷、直播平台和网吧的环境也都变得更成熟,有些主播通过页游的联运广告赚到“电竞行业的第一桶金”。
那份热闹让我对电竞的未来更有信心。
六、撞上风口,但我退场了
2015、16年堪称电竞资本的高峰,有钱人、富二代、资本大佬纷纷涌入,想要打造所谓“电竞综合体”,从直播到俱乐部再到经纪公司一条龙。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再创个直播平台?要多少钱?几千万还是几个亿都行,我们一起干!”
也有人打算用电竞圈热度来炒地皮、搞地产投资。
热衷于“风口概念”的人,花式操作层出不穷,可很少有人真的想静下心来做内容或赛事体系。

我看着这些热钱狂舞,心里却觉得不踏实。
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资本是要看回报的,如果行业基本面还不成熟,只靠投资吹泡沫可能很危险。
最后我选择在17年退出了一线电竞圈,去了心动做投放,亲身从乙方转成甲方,感受另一种角色的压力。

在当时的环境下,找UP主做插入广告非常便宜,导致很多时候预算花不完。
而且当时的up主也非常愿意配合投放,他们会想尽办法的去在他的片子里边把这种植入性的广告做得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是跟我们那个个年代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七、开始纪录片创作
我其实一直比较擅长写人物专访、人物传记,也喜欢记录幕后故事。
2018年,我决定创业做一档专门关注游戏与电竞人物、幕后制作的纪录片自媒体。
决定的当下,就发了一条朋友圈,便很快就拿到了融资。

在我看来,电竞或游戏行业的真相不应只停留在赛场上,还有太多封尘的故事值得被挖掘。
然而事实是,当我真的投入其中,高制作成本与平台流量分成之间的矛盾立刻凸显。
平台方一若发现视频里包含商业植入,轻则不推荐,重则限流。
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广告收入,往往很难真正落到我们头上,播放量也无法覆盖团队开支。

为了维持生计,我们尝试拍一些人们更好奇的话题或网红,从而快速涨粉、获取流量。
虽然后来数据确实大涨,但我内心依旧对“幕后大佬和行业深度”这一块儿念念不忘,总觉得那才是我想要长期坚持的东西。
八、“心动”再拉我一把
2020年的YQ来得猝不及防,团队成员大多是外地人,春节回家后无法返沪。
我被迫解散办公室,暂时停止不少拍摄项目。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进退两难之时,心动“老甲方”又一次出现在我生命里——他们要做一款平台跳跃类格斗游戏,名叫“Flash Party”,希望我跟拍一年研发全过程,做成11期的纪录片。
对我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一种“救赎”。
我喜欢深入团队去拍他们如何设计角色、如何测试打击感,还有团队内部的小争吵、小纠结。“有人愿意出钱拍摄幕后”,还让我“听故事”,我当然兴奋。

尽管这片子在大众平台的播放量一般,但团队内部和玩家社群反响很好。
心动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留下测评、研究与传播价值的内容。
对我来说,这些幕后点滴让我看到更真实的游戏行业,也真正让我在艰难环境里找到了一丝空间。
九、钱从哪来
在“Flash Party”之外,我又逐渐展开“钱从哪来”这一系列,继续聚焦游戏与电竞行业中的不同主体:有强资本背景的大厂,也有寥寥数人的独立团队。
尤其是做独立游戏的这群人,让我深受触动。
他们常常不被外界看好,资金薄弱、技术也许并不顶尖,可就是因为热爱,咬牙坚持了下来。
我想起自己当年在一个没人认可的时代搞电竞,也是一种“草台班子”,却能迸发出巨大生命力。

这些独立开发者在项目反复跳票、经费严重透支时,也常常被质疑“跑路了”。
可当我近距离拍摄时,看到他们依旧会为了一个设计不睡觉,翻书、学程序、挑战架构。
我能理解那份“偏执”,正是因为曾在另一条路上同样颇有共鸣。
十、不放弃记录的理由
我在家里养了四只猫,全是流浪猫,一年捡回一只。
起初我并不擅长照顾小动物,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对我的信任、依赖让我对生活多了一份牵挂,似乎也软化了我的性格——因为我得保证它们按时吃饭、打疫苗、体检。
有些猫平时对人很高冷,可一旦觉得我情绪不对,居然会跳到我怀里蹭脸,传达一种“你别难过,还有我”的信任感。

这种奇妙体验与我拍纪录片的心态也互相呼应。
就算外界再风云变幻、平台政策再迭代更新,我都还有这一群小家伙默默陪伴,还有我的团队和观众在背后支持。
我始终觉得,热爱与坚持本身就值得被记录,不论它能否得到主流资本的青睐,不论数字流量是否能跑赢成本,它依旧是我想做且会一直做下去的事。

导演BK
专注游戏纪录片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